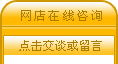中国教育报
郭继民
天下读书人多矣!每个读书人皆有其独到的读书方法,似无须本人在此赘述。但鉴于青年人读书(尤其阅读思想艰深的学术著作,姑且称之为“研究型读书”)确乎又存在诸如“事倍功半”甚至“无功而返”的问题,故笔者姑且以“过来人”的身份将读书经验和盘托出,以期对青年朋友有所助益。
科技哲学家波普尔认为“科学研究起源于问题”,读书亦然,南宋理学家朱熹主张“读书无疑者,须教有疑”,即强调读书须有问题意识。对于学术类的著作,笔者尝以“四问”法践行之。
所谓“四问”,即是说在阅读文本时,读者应采取主动姿态向文本发问。
第1问,当问询:作者想要干什么?读书犹如作战,弄清对方的战争意图,乃是取胜的关键。问询“作者想要干什么”,即在于弄清作者的写作意图。唯有知晓作者的写作目的,弄清“作者想要干什么”,方能较快地进入情况,把握文本主旨。譬如,以阅读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为例,若压根不知著者目的,是极难读懂——甚至压根读不下去的,因为晦涩的语言、繁多的概念、复杂的句式以及独特的思路足以将人拦在门外。倘若知晓康德之目的在于“通过对人之理性能力之考察以解决认知何以可能(知识何以可能)”,那么,在阅读该文本时,虽觉其艰深,但至少阅读时有了方向感。方向感对于读书极为重要,读书有了方向感,方能做到心中有数,不至于坠入云里雾里。
第2问,当问询:作者是怎么干的、干了些什么?具体而言,便是作者围绕其论证的问题或主张都干了些什么,尤其要弄清作者是怎么干的。弄清此问题是极需功夫的,它不仅需要读者反复精读,而且尤需读者对文本下一番解剖学的功夫。其中,“怎么干的”主要剖析作者所采用的思维路向、论证方法及相关的“建构术”。譬如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主要采用追问(逼问)、思辨方式,将问题层层引向深入,后期将思想接引(建构)出来。“干了些什么”,主要是具体内容之构成,可喻作文本之血肉,譬如《理想国》中关于“正义”的辩论,关于“勇敢”的辩论,诸多细节及例证则构成文本的血肉。以笔者经验,若读者能把握住作者的思维路向及论证、建构方法,“干了些什么”即内容的部分还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的:因为方法若建筑构架,内容则似建筑材料。掌握了文本构架,即基本掌握了文本内核。更何况,理解构架亦须通过对“建筑材料”的分析。如此看来,第2问实则包括两个重要问题,即“怎么干的”和“干了些什么”,不过,考虑到方法和具体内容密不可分,故笔者将其合并为一,名之曰“作者干了些什么”。
第三问,当问询:作者干成了没有?此问题的潜台词有二:若作者“干成了”,对后人有何启迪?若作者“没干成”,又存在哪些问题?读者将如何评价文本、评价作者?此一问可谓相当见功底的一问,唯有吃透文本、弄清问题、熟稔作者的写作背景及在充分阅读相关文献基础上,方能有此一问。此一问,同时意味着读者不再亦步亦趋地追随作者,而是开始跳出作者的笼罩和控制,站在评判者的席位上对文本(或作者)解决问题的思路、论证方法及所达到的效果进行评判。
这里需要强调的是,一般作者对经典文本不敢质疑,其实大可不必。经典当然有其永恒的魅力,但亦非尽善尽美,倘如此,人类有一部经典便足够了。人类之所以有众多经典文本,则在于后人敢于对早期的经典进行质疑与评判,从而留下了“别样的经典”。因此,对于经典文本,今天的读者当具有敢于评判的勇气。更何况,作为后来者的读者,在时间序列上具有“后来者居上”的天然优势。正如哲学家叔本华所言,“哲学的情形犹如拍卖房产,结尾说话的人总是使前面的人所说的一切无效”;维特根斯坦亦言,“在哲学中,竞赛的获胜者是能够跑得慢的人。或者,末尾到达的人”。哲学如此,其他学术性文本亦如此。既然作为读者占据后来者的优势,有机会浏览由经典到读者之间所有关于此问题的文献,故而读者应当具备更开阔的视野、更灵动的思维,更应当有信心对作者发起评判性的质问。
第四问,当问询:换做“我”,应该怎么做?如果说“第三问”建基于足够学术储备之上,那么此问则是颇具“创造性”的一问。因为,此问中,作为主体性、创造性的“我”开始登场。此时“我”亦将发生身份的转换,不再以读者登场,亦不再局限于读懂文本、读懂作者,而是在把准文本脉搏的基础上,将文本所涉及的有价值的话题继续进行下去。
冯友兰先生谈到中国哲学的讲法时,曾有“照着讲”与“接着讲”的分判:读懂文本属于“照着讲”,并不增添任何新东西;而“我该怎么做”的问题属于典型的“接着讲”。“我”将接续经典文本的问题,站在时代立场,利用人类所达到的新成果按“我”的思路对经典中的问题进行探索、重新解答,以期给出更为合理的解答。很明显,“第四问”已超出一般读者的要求,而是带有研究性的阅读。
此问意义极大,尤其当“我应该怎么做”落实到“真正地做”时,意味着读者(其实已转变为作者)不仅深入问题,而且以一种实践者、探索者的姿态去将问题引向深入。反观人类学术史,举凡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著作莫不如是,费希特通过对康德哲学的问题的解答、谢林通过对费希特哲学的问题的探索、黑格尔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整合,从而使德国的古典哲学渐次达到高峰;叔本华通过对康德问题的范式转换,尼采通过对叔本华问题的挖掘,弗洛伊德通过对叔本华、尼采的另类诠释,从而将非理性主义哲学提升至一个崭新的高度……
也许,作为普通的读者,似乎难以达到若黑格尔、尼采之建树,但至少“我们”在通过沉思将问题引向深入,并从沉思中得到乐趣;退一步讲,谁能保 证下一个“黑格尔”不在读者中产生?
(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副教授) |